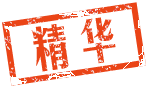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小芳 于 2020-11-5 21:30 编辑
老屋很老,老得我找不到了。只有影像,在记忆里依稀。 白石灰的外墙,间或有灰黑泥石露出,青瓦铺盖成屋顶。有雨的时候,湿漉漉的,青瓦白墙的颜色就会重一点,和门外的泥巴一样。 我和弟弟总喜欢坐在门槛上玩。那是一截光滑的石坎,宽厚的样子,洁净的,淌着黛色的油亮。天气极热了,我们坐在石坎上,借着石坎的清凉润我们燥热的肌肤;雨大一点了,门前屋后泥泞不堪,我们两双小手就把门沿边的清泥捧起,一团一团的,放在石坎上揉捏成面窝状,或抹在对方脸上。雨水从高空溅落,地面似乎无数泥鳅跳跃。我们乐此不疲。 堂屋左边,是爹爹婆婆住的房间,木板模样的门槛有点高。房门旁,是一张我们踮起脚也够不着面的桌子,婆婆把红糖白糖和自己熬制的麦芽糖搁在上面。那时候,没什么美味,晴天里,拿到屋顶晾晒后做成的豆酱,也搁置在这高高的宽面桌上。姐弟俩吃着稀饭,一个端着碗站在门边,站在木门槛上的那一个,一手攀着门框,一手用茶匙从搪瓷缸里挑出些许糖或豆酱,点撒在稀饭里,吃得欢天喜地。 右边的房间,是爸爸妈妈的卧室,红漆衣柜,红漆镜箱,倚墙侧放。天刚擦黑,爸爸就拿出木盆泡脚,他的脚没过水,就开始教我读诗。以前他都是一字一句地教我念,而那一回,他却唱了起来: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------我一时并不能理解,只晓得看着中山装严肃样的爸爸,唱着不好听的音律,真是好玩。我笑得岔气,头碰着镜箱角,疼得想哭又还是笑。我喜欢在这个房间的沙发上歪坐着看书,那是临窗的沙发,皮面是黄黑格子的,有点硬。阳光好的时候,我窝在沙发里,弟弟他们在外面疯跑,我也不管了。 屋旁隔一条小路,便是庄稼田。田里不种秧苗的时候,便种芋头,当田里什么都没有,就是冬天了。下雪过后,我们穿着木屐,走到田里来,即使不打雪仗,不堆雪人,单是听木屐踩在雪地上的“嘎吱嘎吱”声,都会引得我们哄的笑开。庄稼田那边,是个不大不小的池塘。池塘水被抽干的日子,我们在岸边看人穿着又长又黑的下水衣,在泥里挖藕,捉鱼,运气好的时候,捡几条小鱼或几节裹着淤泥的藕回来,是很有成就感的。 快过年了,家家户户都更忙活开来,烟火似乎一整天都不断。早晨做豆皮,薄薄的冒着热气的面皮,用竹篾簸箕顶着,从厨房拿到外面干净的篾席上晾起。实在忍不住口水,想吃也是可以的,只是不能贪多,将一层豆皮撕开一个口子,趁热嚼了,还没辨出味来,又一张豆皮被妈妈端出。她见了馋嘴小女,佯嗔几句,便转身入厨,继续忙碌。午饭过后,可以炒豌豆,炒花生,我就在柴火灶旁站着,看锅里的豌豆在大锅的细沙里跳鱼儿似的跳,看花生壳慢慢红黄。兴致来了,也往灶膛里加点柴,没想到火焰太盛,糊了一锅的花生,让不留神的婆婆跳起脚,双手拍着围裙懊悔不迭,我闻着糊香味,哈哈笑,笑着出厨房。 最有印象的,还是和爸爸妈妈在菜园田里。爸爸负责挑水,妈妈只管浇园,我捉菜叶上的小虫。菜园田离屋并不远,爸爸挑的空桶总是前后晃悠,妈妈就上前把扁担上的绳子拢一拢。这时候,太阳在渐渐西沉下去,村子上空,炊烟四起,婆婆划着柴火,开始淘米煮饭。水沟不深,爸爸将木桶侧身入水,水面立马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,他总是一回只装半桶水,然后就起身;妈妈拿着葫芦做成的水瓢,从桶里舀出水来,在自己面前将水呈扇形模样洒开。顿时,每一棵蔬菜的叶面,便有晶莹剔透的玉珠滚闪,地面也湿了。我立不下脚,赶紧撤到爸爸身旁,爸爸正在跟妈妈说工作上的趣事,妈妈也在跟爸爸说着家长里短。我插不上话,只好找菜叶虫,找不到菜叶虫时,就抬头看天。太阳已经隐没了,远处林子里也安静下来,偶尔几只鸟雀晚归,扑棱着翅膀,引起一阵簌簌声------ 老屋斜对面有一户人家,他们有一台黑白电视机,很威风,他们家门口还有一个大禾场。天一黑,人家就把电视机搬出来,搁在大方桌上,大方桌就摆在他家大门口。门口的灯泡昏黄的亮着,无数蚊虫在光圈里飞来飞去,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灯泡牵着电视机的插头线,他们家人出来进去,都要低着头,他们生怕触着插头,我们也怕,我们怕插头一闪,电视机断电了。有一次,电视剧里女子跟她丈夫怯怯懦懦地低下头来,还没开口,我就脱口而出:我怀孕了!满禾场的人哄笑,我没有一丝难为情,因为这女子后来就是这么说的,我猜中了剧情,我的普通话还不错。 我读一年级了,还没有跟爸爸搬到他的单位住,我们仍是住在老屋。从老屋到学校,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,路的两边,都是高高的笔直的水杉。一般情况下,我都是坐在爸爸肩上上下学。偶尔,他会牵着我的手一起走,走着走着,我就饿了,吵着要吃米粑粑,他不买,我就顺势坐在地上,或者抱着水杉,水杉树皮毛茸茸的,一点都不扎手,我不哭,只说饿了,走不动了。爸爸哄我不住,只好又把我搭在肩上。我双手拍着他的肩,小脚在他胸前抖呀抖的,像极了他的女王。 后来,爸爸妈妈拆掉了这座三间瓦屋,做了一栋四间两层的楼房。楼房做好后,我却随爸爸住进了他的学校。那栋楼房,只在叔叔结婚的那几天很热闹,过后,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我们很少回去了。 偌大的老屋,只剩了爹爹婆婆。 参加工作后不久,我回老屋看望他们,婆婆牵着我的手,满脸慈祥的怜爱,她说:快点带个朋友回来呀,趁我还看得见!我笑,撕着一块面包,叫她慢慢吃。 等我和夫一起回老屋时,老屋已经变卖。我们只是在离屋不很远,不很远的一处,找到了爹爹婆婆的坟茔。我们点起香烛,烧了纸钱,放了鞭炮,我双手合十,心里默念:我回来了,您看到了吗?
|